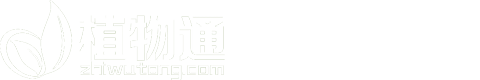植物八题
来源:青春 作者:沈 苇 日期:2008-10-01
土豆幽灵
“它是地府的。”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一书中这样谈到土豆,并将它与小麦作了一番对比:小麦向上指,指向太阳和文明;土豆却向下指,指向地府的幽暗——它的块茎在我们看不见的地下成长,藤叶懒散地趴在地面上。
中国人的常识是吃啥补啥。而法国人则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
——吃土豆补的是什么呢?是地气,还是土地能给予人的种种恩惠?
——吃土豆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能证明“你是什么”?莫非吃土豆的人会变成土豆本身?变成驯化过3000多种土豆的印加人的模样?变成遭欧洲人歧视的疯狂爱上土豆的爱尔兰人?
一般来说,北方人比南方人更爱土豆,穷人比富人更依恋土豆。因为土豆是大地慷慨的赐予,是地窖里的寂寞和充盈;是土地爷的穷亲戚,是煮在水里的胖歌手,是牛肉的恋人……在北方漫长的冬季,是土豆照料了我们的胃口和生活。
在北方,人们有储存冬菜的习惯。菜的品种比较单一,不外乎“老三样”:土豆、白菜、萝卜。如今随着温棚蔬菜的日益普及,这个习惯正在改变,储量也越来越小了。
有一年入冬前,我在地下室储存了两麻袋土豆,足足有一百多公斤。加上一些大白菜、青萝卜和胡萝卜,我想,这个冬天再冷,雪下得再大,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一个冬季,我们一家三口吃掉了整整一麻袋土豆和别的冬菜,却将另一袋土豆忘在了地下室里。除了取菜,地下室平时是不去的。
乌鲁木齐的冬天终于过去了,街上冰雪在融化,树枝吐出了新芽。我忽然想起了遗忘在地下室里的一麻袋土豆。只要不发芽,还是可作盘中餐的。
我打开地下室的门,拉亮了灯,眼前的一幕让我大吃一惊:地下室狭窄的地面上,到处爬满了土豆的芽苗和藤蔓,它们杂乱无章,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有的还爬到了墙上。墙上散发的潮气似乎使它们稍稍安心。
像乱麻,像长蛇,像扭动的蚯蚓,这些疯狂的土豆藤蔓来自那只千疮百孔的麻袋,它们一度突破了束缚,却在地下室弥漫的黑暗中走投无路,绝望地纠结成一团,仿佛在告诉对方:相互勒死算了。这时,哪怕有一丝一缕的光,它们也会奋不顾身地扑过去……
它们一律是黯淡的,惨白的,如同变了形的森森白骨。我甚至闻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与地下室霉变的气味同出一辙。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生命和朝气,只有无助和绝望。
在充满惯性的地面生活中,已经有那么长时间,我忘了自己还有一间地下室,更不知道地下室里发生了什么。而在被忽略的地下时光中,惊心动魄的事情早已发生,并且还在持续。
蛰伏了一个冬季的土豆块茎,一定是在时间和黑暗双重的囚禁中听到了融冰的动静和春天的脚步,用芽苗和藤蔓去寻找自己的出路,却被无情地挡了回来,并被告知:此地无路可走。——黑暗已吞噬了所有可能的路。
我捏了捏麻袋里的土豆,它们是空的,只剩下一层干枯的硬壳。那些走投无路的藤蔓,已经耗尽了块茎所有的能量和养分。
在地下失神的片刻,我呼吸了死亡,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更替和变形。
……土豆幽灵在徘徊、挣扎,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地府中的呼告和诉求:“我的光,我的路,在哪里?!”
沉重的梭梭
梭梭比重大,能沉到水里去。一截燃烧的梭梭散发的热量,相当于同等重量的煤炭。因此,梭梭堪称沙漠中活着的燃煤。
无论是黑梭梭还是白梭梭,一年中要休眠两次。在夏天和秋天,它不停地睡眠、睡眠、睡眠。——是否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因为绝望,只能睡觉?但是我想,这个沙漠里的“瞌睡虫”不是因为无望和倦态,它的休眠实在是出于积聚内在能量的需要。其休眠更像僧人的打坐、入定。
它有自己的花期,但短暂如昙花一现。那些细小的“昙花”,谦逊,低调,粗心的人是看不见的,不像红柳开花时那样铺张而引人注目。
与胡杨、红柳一样,它是沙漠里最顽强的植物,是植物中的英雄。它从不苛求环境,烈日、风沙、盐碱、干旱中正好如鱼得水。它向环境需要的是那么少:一点点水份,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养料。它几乎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指望和索取,连叶子都缩小为紧附在枝条上的小小的鳞片。如果不存在植物必须的光合作用的话,它愿意省略所有的树叶。它的节约是彻底的,对世界它没有一丝贪求和奢望。——它在返回自身,返回自足的内部世界。
它缓慢的生长充满了耐心。它就是忍耐的化身。一截长了二三十年的梭梭只有成人手臂那么粗。因此它拥有坚硬的铁一样的质地、细密的玉石一般的纹理。它短暂地开花,脱去多余的细枝赘叶,吮吸沙漠里最后一滴水……它把忍耐精神发挥到极致,把诅咒变成静静的成长和生命的赞礼。
它习惯于死一般的沙漠,沉浸于生长的快乐中。篷乱的造型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流人,风尘仆仆,来不及梳理一下枯涩纠结的长发。它在时光的寂寞中跋涉,从死亡那边移植过来,在静止中走了漫长的路。它总是这样:享用干旱像享用一席盛宴,扎根荒凉如扎根一片沃土。
如果沙漠是一座监狱,它要把瀚海的牢底坐穿。
它要凭籍自身的重,沉到地底去,变成黑暗中的一块煤。
红柳娃
红柳开花美不可言,粉红或紫红,嫣然枝头,似粟似缨,如火如荼。一处红柳丛就是一个锦簇的花团,一个花的大火炬。且一年开花两次,花期长,从5月到9月,盛放不已。是红柳,用它强大的根须,摁住了沙漠的汹涌起伏;是红柳花,用它绽放的美丽,改变了人们记忆中沙漠的荒凉和贫瘠。
纪晓岚将红柳开花的景象比作“绛霞”。萧雄称红柳是“木之最艳者”,其花犹如紫薇,每枝节处,花如人面,耳目皆具。诗云:“红柳花开莫可俦,白杨风惨易悲秋。”意思是说,红柳花之美不是别的树木能相提并论的。
古籍称红柳为“柽柳”,将“柽”字拆开,我的解读是“木之圣也”。
当我在南疆寻访传闻中的“吉普赛人村庄”时,首先是一路上的红柳吸引了我。它们绵延、相伴在乡村道路两侧,使我走走停停,一步一回头。我曾说过,西域有三种人最美,首先是孩子和老人,其次才是美女。在那个名叫协合力的相对封闭的疏勒村庄,我不得不承认,从来没在别处见过比这里的孩子更像精灵,以及眼睛更清澈更明亮的了。村里的老人,一个个神定气闲,看上去像是白髯飘飘的智者。还有红柳,几乎把整个村庄都给包围起来了。
写到孩子,我不禁想起清代有关红柳娃的传说。
纪晓岚流放新疆时,是西域奇闻的爱好者和收集者,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人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絷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僬侥之属。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
纪晓岚还说,有一个名叫丘天锦的县官,在巡视牧场时得到过一个红柳娃,将其制成标本带回老家。细看红柳娃的须眉毛发,和我们人类十分相像。
《阅微草堂笔记》偏好奇闻野史,不乏道听途说,有某种“搜神记”的色彩。但此前成书的官修地方志《西域图志》对红柳娃也是有记载的:“乌鲁木齐附近深山中,每当红柳发生时,有名红柳孩者,长仅一二尺许,结柳叶为冠,赤身跳踯山谷间,捉获之,则不食以死,盖亦猩猿之属,特不常见耳。”(卷四十七《杂录》)
故此,纪晓岚深信:知《山海经》所谓竫人,凿然有之。有极小必有极大,《列子》所谓龙伯之国,亦必凿然有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