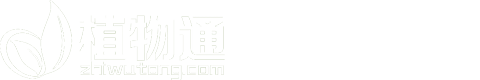和植物一起生长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李开周 日期:2011-06-07
江湖古老相传,南朝美文写手谢灵运长了一部很长很帅的胡子,三绺长须飘拂胸前,就跟美髯公关云长似的。当时有家寺庙正在塑佛教人物维摩诘居士的像,急需一把胡子,而谢灵运刚好信佛,就把胡子割下来,施舍给了那家寺庙。
一部胡子而已,本来没什么了不起,可那是谢灵运的胡子,谢是文坛大腕,文学史上赫赫有名,他的胡子粘在维摩诘的塑像上,那尊塑像也跟着声名大振起来,从此香火不断,香客如云。
话说二百多年后,某个端午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跟闺蜜们斗百草,输了,忽然想起谢灵运的胡子,心说:等我拿出谢灵运的胡子来,看你们用什么草跟我斗!当即派人骑快马赶到那家寺庙,把维摩诘像上的胡子揪下送到京城。
拿到胡子以后,安乐公主究竟有没有反败为胜,历史上没有记载。我猜她是能胜的,因为再稀奇的花草也不能跟一个历史名人的胡子相提并论,那是文物,对不对?她的闺蜜们可能会提意见:咱这是斗百草,又不是斗胡子,你犯规!安乐公主则可能杏眼一瞪:谁规定不能用胡子斗百草?你们要不服,去找陶渊明的胸毛!
我不清楚唐朝斗百草的规矩,不知道是否只能在端午节那天进行,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胡子。我只知道《红楼梦》里芳官藕官她们在大观园斗百草,是哪天都能斗的,她们用的“百草”也是林林总总,星星翠、月月红、君子竹、美人蕉、观音柳、罗汉松……花草和树木都有,是植物就行,不限于草。但胡子是没有的。
斗百草这种游戏,我小时候玩过。我们那儿过端午节,风俗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吃粽子,我们炸油泡。“油泡”是一种面食,面粉里加点儿盐,加点儿矾,搅成糊糊,一抓一团,搁油锅里炸,刺啦一声入了锅,本来扁乎乎的面团马上鼓起一个大泡,所以叫油泡。油泡炸好,先不吃,往祖坟送,大人小孩都去,大人在坟前摆供,我们在坟地里斗百草,斗饿了,那边刚好撤供,于是一家大小在坟前吃油泡。这个风俗比较奇特,可能你们觉得怪异,我倒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我小时候,坟地里不种庄稼,所以就成了草的天下,几乎什么草都长。有一种细长的草,两头尖,中间宽,像织布用的梭子,我们叫它“梭梭草”。有一种低矮的草,叶子很粗,分得很开,油青发亮,根在地下丛生,扎得又深,想把它拔出来,得使吃奶的劲儿,我们叫它“老牛拽”。此外还有蒿蒿棵、甜甜芽、灰灰菜、毛毛根、滴滴翠、天天樱、葛儿秧、燕儿麦、猫儿眼、水萝卜棵、血袋袋棵、小小虫卧单,等等。我们那儿给野草取名有些特点:要么用叠音词,譬如荠菜,在我们那儿就叫“荠荠菜”;要么走儿化音,在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的中间加一个“儿”字,显得那么亲切,跟喊自家孩子似的。
小时候斗百草,没有《红楼梦》里那么高雅,星星翠对月月红,观音柳对罗汉松,分明文人作对子,那是他们上等人的把戏,我很厌恶。我们另有一种玩法:拿草当玩具,看谁的点子最高。譬如俩小孩斗狗尾草,二秃子刷刷刷地把多余的叶片撕掉,然后三扭两转,一根狗尾草就变成了一个小梭镖,再往远处一甩,嗖的一声扎西瓜上了;狗顺子不屑一顾,揪出狗尾草中间那根细茎,扭成一个小圆圈,吐上口水,闪闪发光,放大镜做成了,离地近一些,能看清蚂蚁交配。像这种好玩的游戏,现在的小孩已经很少有人会玩,不光城里孩子不会,农村孩子也不会了,它们就像某些神奇的武功,在江湖上失传已久。
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沈信先生,最喜欢斗百草,七老八十了还大呼小叫跟小孩玩这个,他说:“身入儿童斗草社,心如太古结绳时。”意思是贴近泥土,贴近童趣,无需机心,没有焦虑,是一种岁月静好的大快乐。可惜懂得这种快乐的人实在不多,现在咱们的企业家只懂得“奋斗”,整天忙着把心灵弄脏,把精神弄得很受伤,然后再花很多很多钱去“灵修”。有一部分官员则只懂得把城市扩大,把乡村迁走,驱赶着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每年再砍几百万棵树做纸浆,为的是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森林大面积消失的消息。
现在野草也比以前少得多了,凡是长草的地方都开始长钢筋水泥,小孩子放学之后找不着满眼青翠的野地,只能找到黑网吧和钢琴学校。无论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都很难说出十五种以上植物的名字,他们离植物越来越远,他们接不上地气了。
去年过端午节,我开车回老家,看见公路旁边的坟地还在,但是只有大人摆供,没有小孩斗百草。也许在这一代孩子心目中,与其脏兮兮地去玩草,还不如去玩大人的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