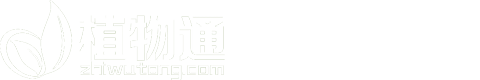植物与《诗经》时候的爱情
来源:海燕 作者:越嫣萍 日期:2005-01-01
荇菜是《关雎》中一组醒目的形象,它们在遥远的古水中,枝叶明媚地漂浮着。荇菜为叶状,一片片,一丛丛,丰茂的色泽演化出朵朵流伞。《诗经》时候,阳光倾泻出干净的米黄色,万物涂着淡淡晕轮;浩然长空,飘着如絮的云;河畔的沙,粗砺纯净,闪着针尖似的光。水流划出了旋涡,委婉露着鱼影;几只脚印隐约消失于岸边,岸在水流冲刷下,遗漏出润湿的黑褐色,阴冷的地方布满了青苔。《诗经》时候,月光牛乳样鲜亮、纯洁;树木浸透于天河般的光线里,丰裕的花草气息将月光织成了静谧的网,河边的虫声与蛙音就挂在网眼里。《诗经》时候,长风翩然,是天地吐合的呼吸,它来自旷野的丹田,饱满而鼓胀,扫过土地、山冈、河流,携着原始的体息。这美好的古典场景,我多少次怀想着。我摸索在《诗经》的字行中,就为回望那尚未沾惹尘嚣的日子。
荇菜匍匐于水流的怀抱,枝叶间流转着阴柔的香气。绵绵荇菜,与水涡共舞,无意间发散了一种情感质地。它飘然嬉闹的样子,将生命气象吐露于小河边。于是,自然之子在缠绵的氛围里,也牵扯出了一种灵性。盘桓在河边的古君子,触于目,感于怀,情思如缕,缠绕环复,如散布在荇菜上的纹理,在季节的水里翻覆、延展、清晰、模糊。但他含蓄、内敛、儒雅、文静,他遏止着自己,环顾四周,又只能将这种无以言状的意绪附着于荇菜,是荇菜的色调、情状激发了他,是荇菜委婉、曼妙的气息感染了他。他自然而然想起了“淑女”,自然而然想让她做自己的好伴侣。但他是才情、品行都很好的君子,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冒昧太唐突,但谁让荇菜那么美妙呢?是“荇菜”让他多情起来——所以,“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多么巧妙的古中国式示爱方式——中国式古典情景,中国式交流意识,中国式男子形象,从文学的童年飘然而来,充满了稚气、童贞。要向钟情的人说出爱,要将内心的颤栗形诸于语言,怎么可以轻易脱口呢?难为情、腼腆、言不由衷都是语言外面丰富的表情,但古君子的气味都很沉静,他们要保持优雅、彬彬有礼的古风度。于是,要先说此,再言彼。要先说出表情达意的类似事物,再说内心真正的思想,要让所爱的人去意会、去体味;要让所爱的人有所回想、有所触动;要让所爱的人沉浸于一种氛围里,像染色一样渐渐染出一番心境;要让所爱的人有回旋、有联想、有悠长清晰的咂摸。当然,更要有一些阳春白雪的意味。于是,自然而然就有了“兴”的表现手法。人在童年时,都有很好的语言天赋,不需要有意学习,就知道怎样揣摩语言的效果,古君子言在此,而意在彼,自觉地找了个小借口,绕了个小弯子,耍了个小手腕,让那美妙的心底情愫附着于神似的物品上,迂回往复地述说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是呀,荇菜的美好让我有了美好的想法,也才让我有了大胆的追求。于是,“荇菜”之类,就凝结成了东方式的含蓄与逶迤,这远古的心理一代代浸润于后人的骨髓时,我们品着《诗经》里的古心声,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仿佛古人的声色就在眼前,《诗经》的表情达意也因此附着了迷人的烂漫气息。
那么,如果是冬天呢,萧瑟的河边还有荇菜吗?洁白的芦苇掠过一袭夕阳的光,岸边的树叶簌簌地落,水里传来“丁冬丁冬”如摇佩环的声音,那是碎冰撞击着河床的情景。清冷的水,发着妖冶的蓝色,冰漂浮于水面,河流成了闪光的凌罗。这时候,君子就说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从春到冬了,绵绵无尽地思念啊,折磨着我,我想着那荇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于是,透过荇菜摇曳的风姿,开始想她的样子,想她的一颦一笑,想她的举手抬足,想她的肤色,想她的姿影,也开始透过视幻看见她。觉得君子喜欢的她,应该是窈窕的,气质应该是清醇的。“窈窕”是模糊的身影,不显山,不露水,像荇菜在水中飘摇的样子,融合了娴静、优柔。窈窕是姿态,也是质地。因此,古君子才能由物及人,浮想联翩。那时,人们背靠黄色山峦,面向丰腴的河水,感情单纯,思想清浅,君子追求着女性原初的骨血,乐也融融,苦也怡怡。其实,生命是一条曲线,人在脱于胎衣后,又向往温暖的回归,爱,就似归巢。那里温暖如桃花源,干净美好,悠然自得。真正的爱就是一方情堡。就像《诗经》没有功利一样,人的情感童年也透明如翼。所以,君子爱慕的“淑女”就是内心酝酿的形象与外在实体的融合,贤淑而贞洁。“窈窕”从文字幼化成人体形象时,同样透出洁净的东方情调。
“窈窕淑女”被他拙而有趣的话语吸引了,她知道,说是“荇菜”牵扯了他,只是一个绿色的借口,也是给自己搭了个台阶,淑女要是喜欢他呢,他就将荇菜抛到了一边;淑女要是拒绝他呢,他还可以继续对着荇菜讷讷欲言,直到遇见属于自己的淑女。其实,聪明的淑女不会戳破荇菜的背面,她只是撩起了碎玉似的水花,羞涩地微笑了。她知道,“荇菜”的色泽将他的心浸透了。于是,她与他幽会。地点选在哪里呢?“淑女”略做思忖,就选在“城隅”吧!不偏不倚,在城角约会,既看得见灯火,又幽僻静谧。
《诗经》时候的城,可能会有城墙,城墙一定也是黄土垒成,黄色是自然的底色,也是人的肤色,背靠黄土原坡,面向河滩田野,也是《诗经》时候的定居方式。童年的建筑逶迤在童年的文学里,关照着人类童年的情感,多么温柔!她是个调皮的小女子,躲藏在墙角不出来,君子略做等待,就急得抓耳挠腮。他踱来踱去,勉强维持着散漫的风度。然而,《静女》让我百读不厌的是,里面也出现了一种植物,叫“彤管”。这是一种红色的管茎草,色泽鲜亮,形体美观,它是淑女送给君子的礼物。于是,君子嗫嚅着“静女其娈(优雅而美丽),贻我彤管”。在君子眼里,淑女美得出奇,彤管也美得出奇。其实,“彤管”无论是什么,一片草叶,一根芦管,一颗果实,都无妨。这里有古人的喜欢,古人的给予,古人的寄托。其实,虽然是一棵草,也与荷包、戒指、耳环、项链价值无异,这些看得见的物件,都是情感的映射。物件是将一份想念浓缩了,变形了,将一份内心情意编织了。物件是什么,并不重要。其实,《诗经》时候,田野里肯定百草丰茂,郁郁如华,她却经过了寻觅,挑选了“彤管”。是“彤管”的色彩、形状一下子抓住了她的眼,她要将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喜欢自己的人,并要传达出内心的一份喜欢。因此,礼物就是能传达自己情思并能保存他人情思的物件,即便选择了一棵草。她远看看,近看看,玩味着上面眩惑的光环,她像放逐鸽子一样将“彤管”放逐出去时,他可以想像,她或许千百次地看过它,抚摩过它,呵护过它。于是,即便一棵红色的管茎草,纹络也出奇地漂亮,形状也格外地美丽。他看着彤管,似乎看见了对方的眼,他想像着对方看着它的表情、神态、心境,觉得奇妙而幸福。其实,穿过光线,这个物件成了两人眼光交汇的媒介,那么,看着它,就是相互对视,相互交流。这是物,又不是物。于是,君子百般珍爱着,而不能仅仅认为它只是一棵管茎草。
这以后,君子与淑女又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确是要成婚了。一个人要走的情感路线,《诗经》中简洁明快地画了出来。读着里面的一些篇章,似乎看着人类远远地走了来。他们走着走着,就将一页历史走完了。姥姥的姥姥,母亲的姥姥,我的姥姥,都有自己的乡村,都有“小河边”的故事,都有“彤管”的风情,他们最终都要走进一种色彩里去,那是一种仪式,是堂堂正正降生生命的引子。读着《诗经》,看见了生命的渊源,人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都要走上一条红色的通道,或者红毡子,或者红地毯,然后吹灭了红蜡烛,于黑暗处,创造一个红彤彤的小世界。星星一样的小世界粘合成了人类的大世界,繁衍成身后的一条河……
《桃夭》渲染了远古的婚庆色彩,“桃之夭妖。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树含苞满枝杈,红震灿烂的一树花。这位姑娘来出嫁,欢欢喜喜成了家。“桃花灼灼”,这浓艳的古国式喜庆场面是不是像一副年画?枝叶间传来了钟音鼓色,喜庆、热闹,曲调高亢,将桃花震开了笑脸。这桃花,在房前还是屋后?在柴扉旁?还是溪水边?总之,它绽开了一树芳华,红胭如织,蕊雪迷离;香气扑朔,蜂绕蝶飞。女子的红盖头,玲珑的红花轿、劈啪的红鞭炮,木格子麻纸上的红窗花,红色米酒与飘着红绸子的唢呐,腾出新鲜蒸汽的红色面塑,厅堂上带了红绒花的绰绰人影,这就是《桃夭》的氛围……女人将鲜红的绳结拴在了新娘衣襟上,祝福他们永结同心。这时候,君子戴着大红花,看着美若桃花的“淑女”,娇俏艳丽,喃喃自语“携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这才是中国人从源头循环至今的一条情感心声,我们无法跳出主流的旋涡。他们从此往后,日息日落,男耕女织;鸡鸣犬吠,红袖添香;炊烟袅袅,溪水淙淙。不多时,便绿树成荫,子女成群。这样读着《诗经》,就觉得,几种植物其实是与情感同在,与家庭同在,与历史同在。
“卷耳”在《诗经》里出现时,情感之流遽然变音。卷耳就是卷心菜。在我的意想里,它是白色底子,绕着绿色纹络,丰富的水气,让它有了一种瓷实的外形,有一种诉说的气势。
“桃夭”气氛渐渐平复了,情感涟漪渐渐淡化了,也许,有些君子习惯了生活节奏后,淑女也渐渐变成了女人。有些君子,就渐渐厌烦了眼前的生活,淑女的体态、性情也与“淑女”相去甚远,无法再让君子想像、激动,“荇菜”、“彤管”、“桃夭都成了回忆,可回忆又有何补益呢?”所以,古君子的风范就渐渐保持不住了,眼睛渐渐掠出屋檐时,就想去河边观望别的淑女了。这时候,守侯着一群子女的妇人又能如何呢?我们于有远处的山冈上,看见了一些无奈的身影——“采呀采那卷耳菜,却总装不满簸箕一样的小筐子,哎!思念着那外出的人啊,将筐子放在大路旁。”
“外出”?去了哪里?其实,人并没有走远,可是,心游移了,神恍惚了,眼光散漫了,妇人与子女都无法使他聚起情感焦点,这种身心的分离也是“出走”,是心神的出走。他已经不愿完全接受她,她也在言行中,感觉到了疏离、陌生,乃至一些有意的伤害。她措手不及,无言以对,只能走出来,拎着小筐子,去不远处的缓坡上采那卷耳菜。这里可以看见他落落寡欢的身影,可以看见她小小的院落,可以听见孩子们的笑闹。她一片片地采摘着叶子,无心看叶尖上颤栗的露珠,无暇顾及草丛中跳跃的虫子,她于埋头采集中,回想着小河边的荇菜、彤管、妖冶的桃花……她一点点地采着,一遍遍地想着,内心的焦虑稍稍有了疏散,她借采卷耳的过程转移着心中的烦乱。于是,“卷耳”成了内心情感的承载者,采着卷耳,就将淤积于心中的块垒渐渐迁移了出来。——“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可是,毕竟不是为采卷耳而来的,所以,采呀采呀,夕阳落下了,薄暮笼起了,内心总是缭绕着难以排遣的惆怅,眼在搜寻,手也在采摘,可总是采不满小小的簸箕一样的小筐子。
也许,君子外出,是征战去了,所以,久久不能回归,卷耳菜附着的情感就沉重多了。女子们在家里坐卧不宁,寝食无味,呐喊、厮杀、血腥蛇一样啮咬着她们的心,她们不敢想像可能发生的事情,只希望远处的人快快回归。于是,只能借助于手中的活计转移一下凝固的思绪,去做什么呢?树杈上正好挂着一个小筐子,采卷耳去吧,采满了就回来。屋对面的山坡上,虫啾啾、草茵茵、风习习,握住卷耳的叶子时,缕缕绿色在指间流淌着,指缝里、手腕间,草汁斑斑,一点点浸润着肌肤,润泽着心灵,奔涌的急躁渐渐平复了下来,内心的焦灼稍稍有了些缓解,那绿色能抚摩心,安慰人,听人内心的诉说。因而,远方的人啊,你可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天天来这里采卷耳,也在这里天天将你眺望——采呀采呀采卷耳,怎么也采不满小筐子,月亮爬上了小山冈,路口还是看不见你的身影,听不见马的鸣叫……
也许,君子永远的走了,怎样走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所以,一边采着卷耳,一边呼唤,远方的人呀,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赶快回来吧!你赶紧回来!心里这样默念着,最简单的重复的心声外化成了手中的采集动作,声无止息,筐子怎么能装满呢?——“采采卷耳,不盈倾筐”,采呀!盼呀!那种深不可测的期盼掩藏在机械的形体中,采集卷耳成了发泄思念的方式,成了转移,成了倾诉。卷耳在她们眼中成了一种寄托,一种发泄。她也许一边采着卷耳,一边就想起了有着荇菜的河水,想起了闪着月光的城角,想起了桃夭的日子,想着想着,手中的卷耳菜还是不能装满筐子,那是掩藏心事的动作,却不是动作本身的指向。
荇菜、彤管、桃夭、卷耳,这些植物像《诗经》一样古老,色泽鲜艳,通人性,总在合适的时候,诉说人的心声。荇菜让难为情的君子有了表述爱慕的好借口,逼真神似;彤管让淑女借机传达了情感态度,完成了心灵嘱托;桃夭更美好,释放了吉祥如意的喜庆色彩,也使新生命有了美好新鲜的初始;卷耳让人在焦虑时,通过倾诉与转移,情感关隘渐渐通融。古老的《诗经》时候,植物与人和谐相处,影射出了纯然的精神状态,妙不可言的交流,使人在空间上与自然有了妙不可言的融合与体认,人与植物、植物与人,都是同一空间的自然之子,人在植物之中回到了自身,情感之花也层层绽开。这是语言智慧,也是生存智慧,心灵的自然状态与植物的自然状态相通时,人是最幸福、最舒展的,最自然的,古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