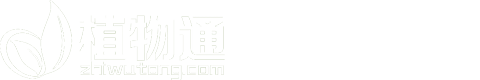踏遍千山人未老 植物学家吴征镒
日期:2013-03-10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石头墙上,“原本山川,极命草木”8个大字泛着光。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不自禁地看上一眼。看见它,会想起吴征镒,也会想起他一辈子践行的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的科研精神。
如果把吴征镒对植物的研究从小时算起,那他在这个领域,已坚持了近90年。在他70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从来没有一天远离过植物
儿时的好奇、青年时入门、成年后的痴迷,使吴征镒的一生都绘满了让人心醉神迷的绿色。曾经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这是多么崇高的褒奖!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植物伟人一路留给中国乃至世界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的财富吧:
他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参与组织领导《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户口本。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他担任了17年的主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尤其是第一卷要概括已出版的前79卷成就,最难写,是他亲自承担。此外他还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
他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问题,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等创新观点。他对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的论述,是植物学、生态学领域的经典篇目。
他为我国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参加和领导了海南和云南的橡胶宜林地考察,又参加了西南特别是云南的生物资源调查,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建立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倡议,又向国家建议建设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对具体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也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具体意见。
他创新性地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纲新系统和植物区系的多期、多系、多域的起源理论。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评价吴征镒。
选择科研,就是选择寂寞。这句被每个科研工作者奉为格言的经典,在吴征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一天远离过植物,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植物所的资料室里,有几个陈旧的书柜,装得满满的都是小卡片。翻开一张,正面是黑白的植物标本照片,反面是拉丁文、英文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还有的,没有照片,只是在些随意捡来的纸张,画有青天白日的废旧文凭,烟壳的背面、不知是什么的小纸片上,写着植物的拉丁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这就是吴老在联大期间整理和鉴定的卡片,这里仅是一部分,北京和南京还有。”吴征镒的第二任秘书,74岁的吕春朝正在整理这些宝贵的资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还未完全扫描进电脑。
从1940年一直到1950年,吴征镒用整整10年的时间,对照老师吴韫珍抄来的中国植物名录文献及秦仁昌氏的照片,整理和鉴定了3万多张植物标本卡片。“这些卡片,成为后来编撰《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最基本的素材。”吕春朝说:“这些卡片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中国植物的最初采集者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16至18世纪时,这些标本被海关官员、传教士大量带到国外进行鉴定发表。而吴老做的,就是将这些本来就该是中国植物的标本重新整理、鉴定,让它们真正成为可以为中国植物研究采用的东西。”
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科研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以坐10年的冷板凳,做一项没有人做过也少有人关注的事,需要多大的兴趣和毅力?对此,吴征镒却说:“栉风沐雨、饮饿劳顿、板凳硬冷、默默无闻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我快乐,从而使我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吴韫珍先生的宿愿。”
成长于时局动荡的旧中国,吴征镒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其踏遍千山万水,找寻中国植物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觉得已耽误很多时间的吴征镒,在这来之不易宝贵年华里分秒必争,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科研。他马不停蹄地行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高原河谷。花甲之龄时还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足迹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和塔什库尔干的沙漠里。80岁高龄时,还去台湾考察植物。他4次进藏,最后一次已是花甲之年,最终出版《西藏植物志》。他行遍除非洲之外的全球四大洲,和全球植物学家交朋友,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水平。
1956年,前苏联专家来云南考察,在德宏,从未见过亚热带植物的他们惊叹不已。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只要他们手指向任何一种植物,吴征镒都能迅速地报出这种植物的拉丁名。苏联专家送给他“植物电脑”的美誉;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科学家拿出了他们鉴定许久却得不到答案的几个标本,吴征镒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英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植物电脑”所称不虚;在日本扎幌,70多岁的吴征镒还未走进城边的小树林,便对同行的日本科学家说起了这里必然会生长的植物,让他们大为吃惊……
“植物电脑”、“活字典”这些雅号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是必然。在植物所,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个他科研只争朝夕的小故事。在北京时,他一直兼任着北京植物所的领导职务。开会时中间有个10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他总是一分钟都不耽搁,马上冲到底下一层的标本室拿起标本进行鉴定整理。有时忘了时间。来昆明后,这个习惯没有改,又多了一个习惯。周日休息时,他可以从早到晚泡在标本室里,直到夫人在楼梯里大叫:“老吴,回去做饭了。”他才磨磨蹭蹭地回家。家里人对他不知晨昏的伏案工作很无奈,为了让他多起来走走,夫人女儿轮番规定他,洗碗去、扫地去。他总是好脾气地把该做的事做了,接着又回到书桌前。
78岁的武素功老师年轻时常与吴征镒一起去野外调查。“他这个人,从来不知道疲倦一样。爱做笔记,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在车上也是,很少和别人聊天。我们去西藏考察回来后,有机会去青岛疗养。他离开北京时装了一皮箱书,我就知道这个疗养可疗不好了。我们住一屋,他中午从不休息,就坐在桌前整理西藏带回来的标本。累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疗养一个月,他竟然整理出了一本《西藏植物名录》。”
“他是植物地理分类学最伟大的践行者,所以很多地方即使他没去过,他也能准确地说出该区系的植物。”弟子孙航对老师很敬佩。孙航在做雅鲁藏布江植物科考时,曾在那儿找到一棵松果带了回来。他找到吴征镒,说这是一棵高山松。可吴老却很肯定地告诉他绝对不是,这棵要么是一种新种,要么是南亚的松。事实证明吴征镒是对的。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到90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时进行劝阻,他要么装着听不见,逼急了就发一点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不服老”的老人,让医护人员也没办法。
2007年,吴征镒91岁了,应任继愈先生之邀,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典》的主编。此时,吴征镒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他参与这项繁重的工作,但是吴征镒说,“我不做,谁来做?”为了编出让自己和世人满意的书,他倾其全力,开始重读清代《草木典》。2007年,吴征镒只能看清3号加粗大字了,医生对他说一定不能过度用眼了。可他却回答:“我再不看,就没时间了。”仍天天据案疾书。到2009年时,吴征镒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他便让助手念给他听,他再据此鉴定整理。一直到2012年3月,他因身体不适再度入院,也从未停止过手头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吴征镒很遗憾,遗憾他只开了个头,而没能干完。他对助手说:我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做完这项工作,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大典·生物典》出版。
“为人学,学为人,先立志,后献身。”永远是一个开拓者而不是一个享福人,认准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终身,吴征镒用他的行动,传达了他对科研无悔的坚定执着。
岁月如河,或疾或缓地滑过吴征镒辉煌的一生。责任如山,中国植物研究之重担却从未卸下他的肩头。一辈子与植物的情缘,一个多甲子与云南的情缘,使吴征镒和这方山水越发相融无洽。如果把他看作一座山,那该是多么多姿多彩的一座山啊。
在同行研究者眼中,他是个真正的大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包罗万象,胸襟广博,坚定担当。他无私地亮出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同行。他倾心教授后学,没有一私保留。而在朋友和家人眼中,他也是一座山,宽厚、大度、深沉、隽永。他情感丰富,爱父母家人,爱植物世界,也爱平凡生活。他唱昆曲、摄影、收贝壳、吹笛子、写格律诗。在世人眼中,他是一座永远让人充满敬意仰望的高山,镌刻着执着和奉献。
(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