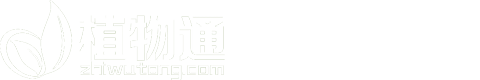北京的植物名片
来源:生命世界 作者:王 辰 日期:2008-08-01
2008年的夏天,奥运无疑成为了北京的名片,而当我们向外国友人介绍这座城市的同时,更多属于北京的名片便显露出来——年代久远的故宫、天坛、颐和园自不必说,年代不那么久远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甚至胡同、四合院也成了北京特色的观赏之处;老北京的吃食也是这城市的名片,享誉四海,炸酱面也好,豆汁焦圈也罢,北京烤鸭干脆挂上了“北京”的名头;就连野生动物之中,也找出了个名为“北京”的——北京雨燕,虽说是楼燕的地理亚种,但毕竟也算北京特色,于是改头换面,北京雨燕摇身一变,成了福娃妮妮。
于是,当我们面对着北京城街道两侧来自五湖四海的国际友人,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观赏布景花卉,面对来自南美的矮牵牛、来自墨西哥的万寿菊、来自巴西的一串红和来自欧洲的雏菊,我们如何向国际友人夸耀北京的特色呢?雅典奥运会冠军可以获得一枝油橄榄的枝叶,北京奥运会的冠军莫非只能获得一束全球花卉市场上都能见到的精美鲜花?
以“北京”为名:树木篇

北京花楸如今的拉丁名字翻译过来,似乎应该叫做“异色花楸(Sorbus discolor)”了,但这种开白花的乔木,曾经确实拥有过“北京花楸(Sorbus pekinensis)”或者“北京梨(Pyrus pekinensis)”的名字。尽管北京花楸的分布远远不只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乃至甘肃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阔叶林中,都能见着此物,但这一植物的模式标本却的确来自京郊,因此也算得上多少有些北京特色。
北京花楸虽然算不上什么强大经济效益的植物,但它的近亲花楸树则可谓风光——木材可制作家具,果实可以制作果酱、果酒,而作为树木本身,花楸树更是在东北的一些城市(例如长春)被栽培用作行道树。其实北京花楸与花楸树相比,除了果实成熟后是白色或黄色(花楸树果实红色),此外并无多大的本质区别。假设,将北京花楸引种下山,栽种在道路两侧,当国际友人们漫步于北京街边,抬头望去,苍翠的绿叶深处,有些微白色的果实,问之,答曰,此北京花楸是也!那种气势,想来会让人挺硬腰板儿,不至于像如今,抬头一看,什么树,答曰,刺槐,原产美洲的。
相比之下,享有“北京”之名的木本植物里,比较风光的当属北京丁香(Syringa pekinensis)了。与北京花楸类似,北京丁香的分布范围,也是在华北及其周边省区,甚至能抵达甘南、川北,但所谓无独有偶,北京丁香的模式标本同样源于北京,连学名的种加词,也是“北京”的拉丁化写法。在野外的北京丁香或许多为灌木状,但在北京的诸多庭院里,尤其是带着古香古色之地,年代悠远的北京丁香却都能长成两三层楼高的小乔木,每逢花期,馨香四溢,微风拂过,落英缤纷,于是也无怪北京丁香自古为人喜爱。如今在国际友人聚集的雅宝路、秀水市场附近,穿越三两条小街,带着国际友人游逛日坛公园,就能看到高大的北京丁香,就能挺硬了腰板儿自豪一下,这东西是从咱北京城出来的!
带着“北京”名头的树木之中,较为尴尬的是北京杨(Populus × beijingensis)——由钻天杨和加拿大杨杂交而成的种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杨,本是被寄予了速生的厚望,经过实验,也确实令其在10余年就可长到20多米,但作为木材,北京杨无疑带有鱼腩之嫌,所谓临阵磨刀,快工出不了细活。而且经过在华北、西北和东北多处的实验,证明北京杨在土壤水肥较好的环境中,方可迅速生长,对于寒冷、贫瘠、盐碱的适应能力并不理想,因而如今即使名为“北京”,在北京地区,北京杨反而并不常见,倒是它的亲本之一加拿大杨,栽培的更为广泛。

此外的一些乔木灌木,诸如北京锦鸡儿、北京忍冬、北京小檗、北京槲栎,也都带着“北京”的名号,无奈的是,如今的北京街头,尚难以看见它们的身姿,倒是它们的外国亲属们在装点着北京街道——譬如原产于日本的日本小檗、紫叶小檗。
以“北京”为名:花草篇
单纯就观赏性而言,以“北京”为名的植物中,也可以找出一两个值得说道的种类,北京假报春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北京假报春(Cortusa matthioli ssp. pekinensis)又名京报春,虽然 如今被划归到假报春的名下,成了假报春的亚种,但曾经也确有人认为,这植物该单独立为一个物种,于是才有了拉丁意义上的“北京假报春(Cortusa pekinensis)”的名头。尽管如今的植物志中,常把北京假报春称为河北假报春,而模式标本记载也是来自河北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花冠紫红色钟形的野花,只要带着pekinensis的拉丁名,就无法抹去和北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北京假报春生于树林边缘、溪流或者灌丛,尤其在树林与亚高山草甸的交界处,时常能够见到。假报春属和报春属同属于报春花科,因为雄蕊生于花冠筒的基部,因此被单独划分出来——但这并不影响假报春的形态为人所喜爱,也同样不影响这种生于山上的植物像很多种类的报春花一样,喜欢寒冷,为引种徒增困难。北京假报春在平原栽培,经常因为夜温过高导致死亡,因此要将这种带着“北京”名头的野花驯服,估计免不了园艺学家们狠狠下一番功夫。

当然,更多名带“北京”的花草,是园艺学家们根本不甚关注的种类,比如北京堇菜(Viola pekinensis)。这种春季开花的小草本植物其实甚为常见,在京郊的低海拔山区,巫师白帽子一般的花朵,时常出没于林下或者岩石缝隙中。只是北京的野生堇菜种类着实不少,多数踏青的游客并不能区分哪个才是所谓的北京堇菜。北京堇菜也是模式标本出自北京的种类,分布的范围却狭窄了许多,除了北京及河北省,只有陕西的太白山有所记载。
还有些小草本以北京命名,它们因为或多或少具有些药用价值,因而间或为人所惦念,例如北京黄芩(Scutellaria pekinensis)、北京延胡索(Corydalis gamosepala)和北京元胡(Corydalis caudata)。北京黄芩号称模式标本采集自河北,拉丁名称也赫然带着pekinensis,分布以华北为中心,可达陕西、浙江、吉林;作为黄芩属的一员,北京黄芩也可入药,药效与知名的中药黄芩相同,主清热解毒。而北京延胡索和北京元胡(又名小药八旦子),则都是紫堇属、实心延胡索组的植物,若是对于中医药略有关注,对延胡索的名头应有所耳闻,具有活血、利气、止痛之效。虽然拉丁名字并没带有北京字样,但这两种延胡索,模式同样都来自北京。
搜寻北京特产
其实,以北京为名的树木或者花草,即便模式出自北京,但就分布区域而言,往往是以华北为中心,有时波及到东北、西北或者华中地区。若说那种植物能算北京特产,因为一个“特”字,几乎可以把所有种类都排除在外——因此,略微放宽些范围,倘若一个物种仅仅分布在北京及河北,就勉强算作北京特产,那么这样的特 产植物,还真能搜罗出来几个。

北京水毛茛(Batrachium pekinense)无疑算是北京特产的代表种类了。中文名字带着“北京”封号,拉丁名字带着pekinense,而分布区域,模式标本采自北京,在《中国植物志》上的分布区域,干脆写明“产北京南口至居庸关一带”。当然北京水毛茛也在其他地方生长,比如松山自然保护区,比如河北怀来县或者赤城县,其生长环境,是山区的溪流之中,植株沉于水下,每逢开花时节,花梗挺立出水,开白色五瓣小花。

若说作为水草的北京水毛茛并无实际作用,其实也并不为过,它们的存在除了生态学和植物分类、系统学上的意义之外,实在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来证明北京弹丸之地也有特有植物种类。但相比之下,虽然不具备“北京”的名头,槭叶铁线莲(Clematis acerifolia)则更为人所关注。槭叶铁线莲,在京郊本地人的口中,被称为“岩花”或“崖花”,生于直上直下的石壁上;自19世纪以一份采集自北京百花山周边的标本被命名以来,槭叶铁线莲一直被认为特产北京,直至20世纪末,在河北地区周边陆续更新了分布。与北京水毛茛相似,槭叶铁线莲的花也是白色,不同的是,槭叶铁线莲始终为一个特殊人群所关注——铁线莲属植物作为西方园艺学家的钟爱,引种、栽培、繁育从未间断,如今无论是欧美还是我国,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铁线莲的人们都不在少数,其中特有的槭叶铁线莲更是为人所惦记,因为生存环境特殊,人工繁育槭叶铁线莲尚未见有大规模成功的报道。

类似的北京特产,或称为北京及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部分地区特产的植物,其实还有20世纪末才发表新种的丁香叶忍冬、记载产于“北京一带山地”的羽叶铁线莲、山葡萄的变种百花山葡萄,其中丁香叶忍冬的记载中未见果实,有关羽叶铁线莲分布的记载语焉不详,而百花山葡萄被认为仅存那么一株,一些调查研究尚在开展之中。事隔了二三十年,再来细数北京的特有植物时,丁香叶忍冬花朵的标本已然存于标本馆中,而百花山葡萄也被发现了第二株第三株所在。
回归到关于奥运会的畅想:当冠亚季军登上领奖台,脖子上挂着奖牌,一手抱着福娃,另一只手里捧的花束,会不会是一枝槭叶铁线莲,或者是一个装有北京水毛茛的小鱼缸?纵然北京特有的花草树木不在考虑之列,至少我们可以奉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花束,就像福娃里面的大熊猫和藏羚羊,我们可以向奖牌得主递过去一枝银杏或者水杉,再不然可以是梅花或者牡丹。
或许,该是拭目以待的时候了。■
(责编窦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