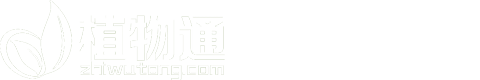南方植物(三篇)
来源:海燕 作者:周根红 日期:2008-07-01
周根红一九八一年十月生于安徽安庆。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作品散见《文学报》《散文诗》《长江文艺》《西南军事文学》等报刊,多次获奖,并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散文诗》等多种选本。曾参加第七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艾
艾,在民间的肌肤和穴位上,冒着一缕隐隐的白烟……
黄钺《南方植物》
我一直喜欢睡懒觉,无事时睡到上午十点十一点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要是冬天,可能会更晚。记得小时候怕冷,赖在床上不起来,竟然让母亲帮我把饭端到床跟前,吃完了再接着往被窝里一躺。然而每年有两个时间我是不敢这样睡的。一个是大年初一,一个是端午。大年初一是一年的起始,自然要为新的一年做个良好的开端,开端完了以后还是一样的老面孔。而端午这一天,是因为一株株艾草。
这天天还不亮,母亲就早早地把我喊了起来,递给我一把镰刀,说,走吧。我便很不情愿地跟在母亲的后面,一直跟她走向山坡。一路上我不说话,我知道母亲让我去干什么。只是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我就问母亲,母亲告诉我说,要趁天亮时去,这样沾着露水的艾草是最能去病的。而且一定是插到门上越早越好,这样妖魔鬼怪就不敢来了;要插得晚了,鬼怪就进了家门,一年都不会顺利的。母亲说这话时,让我觉得,母亲不仅对农事很精通,对乡村的风俗也很熟悉。我只是听母亲的吩咐,按照她说的做。在一个孩子心中,母亲的话其实比父亲的话更容易听进去,父亲的话只是一种威严,骂过打过就完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而母亲的话是润物无声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站在山上往远处望去,目光里满是绵延不绝的庄稼地,有收过麦子的麦茬,还有刚刚抽穗的包谷。那些艾草挤挤挨挨地缀满田埂和山坡,远远地泛着银光,透着油绿,叶片毛茸茸散发着一缕缕香味。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弯下腰,两脚叉开,开始去割艾草。可我的姿势总是让母亲不满意,我总是蹲着,弯不下去,母亲总是说我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干什么都不像。我才不管这些呢,我想着能把艾草割回去就行了,至于姿势美不美我倒不在乎。渐渐地,我看见远处有不断起伏的背影,像是夏天田野里割稻谷,全是清一色的母亲和孩子,她们都在割艾草。那时我还没多想,为什么都是母亲和孩子,其实这些活母亲一个人就可以做的。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淡着衣”。只是我对艾草的感触比较迟钝。长大了才听别人说,我小时候每年身上都长满了疮,母亲听人说用端午艾草上的露水洗脸洗身子,一年四季都不会生疮生痒。于是,母亲就用艾草泡成水给我洗浴,我也就真的再没生疮生痒。也许其他的母亲也怕孩子生疮生痒的吧。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走在割艾草的路上时,我真切地感觉被母亲粗糙的手紧紧地牵扯着,满世界都是母亲从五月的田野里归来时,遍身艾草的气息。那是母亲生病时,我回家看她。母亲躺在床上,告诉我,过两天就是端午了,你去山上割点艾草回来吧。那天,我起得比往常都早。我想母亲一定希望我是第一个去割艾的人,割的艾草一定要都沾满了露水。那一天,我不敢说我是真的第一个,但在我目力所及范围内我却没有见到其他人。我割完满满一簸箕回来时,我看见许多人才刚刚出门。我回来告诉母亲,我是第一个去山上割艾草的,艾草有许多露水,可新鲜了。母亲躺在床上笑,说,好啊好啊好,这下你们今年就不会生病遭灾了。看见母亲这么高兴,我感觉,这些年来,这是我给母亲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韭菜
如果时间是一条河流,如果我割下的韭菜流出的同样是血……
黄钺《南方植物》
如果让你在一个盘子里做十样菜,你会做什么?这是小时候母亲不停给我们几个孩子说的谜语。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我们都没记住,母亲就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说,就是韭菜炒鸡蛋,韭菜就是九样菜,加上鸡蛋,正好十样。说完,母亲就高兴地笑了。然而我们还是记不住,还是让母亲反复解释。
在乡村生活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没吃过韭菜。确切地说没有谁没吃过韭菜炒鸡蛋。小时候,每到夏天韭菜下来了,家里只要有客人或亲戚来,母亲总会去菜地里割些韭菜,再在抽屉里拿出两个放了很久都舍不得吃的鸡蛋,做上一小盘韭菜炒鸡蛋。这是那个年月唯一的一道荤菜。母亲炒菜时,我们几个孩子就在灶台旁转悠着,等着吃那锅铲上沾着的韭菜。当然,母亲也会让我们尝一下盘子里的鸡蛋,可惜我们不能常吃。于是我们就盼着天天有客人来。不过我们吃得最多的还是韭菜煎饼。母亲抓一把切碎的韭菜,用水一冲,往煎饼中间一横,再抹上自做的酱。这时饿极了的我拿起煎饼,赶紧往嘴里一送,猛地用力一咬,一股浓重的韭菜味立马钻出鼻子,那种快意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
这便是韭菜的气息。韭菜就是这样最具有乡村气息的一种植物。她的名字就跟小时候邻居家的女孩名叫翠翠一样,很朴素地弥漫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娟秀,它的美是隐约的,朦胧的,像春天静夜里的融融月光,有着内秀和羞涩的韵味,不像辣椒那么张扬和泼辣。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菜园里有好大好大一块韭菜地儿。每到初春,母亲便早早地除去韭菜地里的枯枝败叶,均匀地撒上那么一层草木灰,然后施一些家畜肥料。几阵春雨,把草木灰凝结成一片浅灰色的地表。细细一看,其中隐约有一簇一簇嫩紫色的花朵盛开在白色的憧憬之上——那便是韭菜吐露的新芽。母亲不明白“春雨剪春韭”的诗句,然而母亲却对剪春韭有着独到的理解。母亲不让我们这些孩子去菜园割韭菜,她怕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割一撮,破坏了韭菜的根系,影响下一茬韭菜的生长。母亲割韭菜总是将一簇韭菜收拢成一束,然后用刀在韭菜叶柄离地约半厘米处利落地割断。母亲边割边说,韭菜是越割越长,越长越长。
我们也像韭菜一样越长越长,一直长成大人,然后我们的孩子也像韭菜一样长出了地面。做了外婆和奶奶的母亲,又给我们的孩子讲韭菜炒鸡蛋的谜语。母亲问,如果让你在一个盘子里做十样菜,你会做什么?我们站在一旁听着,孩子们没听过这个谜语,就一脸茫然地看着母亲,等着母亲说出答案。这时母亲扭过头来问我们,我们就摇头说,都多少年前的谜语了,哪还记得啊!母亲就对着孩子,也对着我们这些大孩子,高兴地说,那就是韭菜炒鸡蛋!然后哈哈大笑。这个谜语也许书本上永远不会出现,可是母亲却说得很认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我们也一遍一遍地摇头。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跟母亲说,其实我们早就记住了,只是我们不说,我们只是想跟母亲多说一句话,想让她在说出我们都不知道的答案后高兴地笑一下,笑得像一个孩子那样天真。
水浮莲
正因为没有根,在文字之内,我竟始终无法把它固定下来。
黄钺《南方植物》
我至今还不知道水浮莲的学名是什么。我也没有去查过,我觉得那些都没有意义。就像村子里的一个人,人们喊他刘二,他会很自然地应一声,可如果你哪天喊他刘瑞喜,他可能会认为你是在喊别人而充耳不闻。水浮莲这个名字就是这样。
母亲常跟我说,水浮莲是一种贱命。你不需要像庄稼那样给它施肥,给它锄草,你只是任由它长,任由它漂,只要有水,它就能长得漫河都是,仿佛那是它一个人温暖的床,然后在这温暖的床上蔓延出一年四季青葱和嫩绿的美好心情。水浮莲就是这样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它只是自然地生长着,它的生长是最接近生活本质的,它只有一个想法,生出来,便活下去,便长起来。
然而正是这样贱的一种植物,却最适合在乡村的水面上生长,只有乡村,才有那么多流动着的水。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些植物都一撮撮地绿在小河里,绿在水田里。那时的乡村,是一个四处野顾无人的地方,放眼望去的只是绿,只是挡住视线的水稻和麦子。这些绿就在其中游来荡去,像一叶叶扁舟。它们跟乡村一样,坚韧而长久。每每看到田埂边的浮萍时,母亲总会说上一句,多像水浮莲啊,只是比水浮莲要小,不厚实。
其实,母亲想说的是,浮萍太不够分量,吃多少都吃不饱。不像水浮莲,一两个就能把肚子填饱。母亲这样说,是因为母亲吃过水浮莲。那是她在生产队的事情,那时母亲总是吃不饱。父亲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给母亲偷玉米偷高粱偷山芋,在什么都偷不到的时候,就偷河里的水浮莲。母亲吃过许多水浮莲,然而庆幸的是没有被抓住过。我一直不相信,也许是母亲不愿意说出那些受过的苦吧。母亲一生经历的事情很多,然而她跟我们说的却很少,偶尔说一下,也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总是陪着母亲去池塘里捞水浮莲。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套着一小块鱼网,用绳子或者用铁丝扎好,我就这样一网一网地将这些植物打捞起来,然后洗干净了回来喂猪。母亲每次看见成堆成堆的水浮莲时,总是很高兴,说,猪有福了,水浮莲那么甜的。我知道母亲说这话时,她的脑海里一定也闪现出那些荒凉的记忆吧。不过猪确实是真的喜欢吃。很多时候母亲都不用煮熟,打捞回来直接就扔在猪圈里,那两头猪就争先恐后地抢着,生怕自己少吃了一口。
终于有一天,我家再也不养猪了,那猪圈也用来改造成了杂屋,用来堆柴禾放农具放化肥什么的。我也很少能再见到水浮莲了。然而我一直记得母亲说的话,那东西命贱得很。其实我知道,母亲也是在说她自己。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