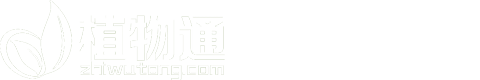植物与思维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作者:崔明昆 杨雪吟 日期:2008-02-01
[摘要]植物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在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即植物文化。本文在回顾“原始思维”之争和认知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应用认知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了民间植物分类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以具体的田野资料比较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异同,得出了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都是人类认识植物的正确方法的结论,这从根本上驳斥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儿童思维”的西方种族主义观点。
[关键词]植物;思维;认知人类学;民族科学;民间分类
[作者]崔明昆,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杨雪吟,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56—008
自人类诞生以来,植物就与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也表现在人类认识和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植物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了民间植物分类过程中土著民族丰富多彩的思维特点,并以此说明了土著民族思维的逻辑性。
一、“原始思维”之争与认知人类学
(一)“原始思维”之争的由来
“原始思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问题。其实,人类学的诞生就与探讨此类问题有关。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就标志着学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人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对原始文化的简单认识,目的在于收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西方儿童思维”模式的证据到认知人类学者对土著民族仔细的田野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第一手资料,并从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中寻找生态智慧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为止,转变之巨大令人吃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法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是因为,书中到处充盈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列维一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最初念头竟然来自他读了法文译本的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史书在他的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维的模式标本,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代的部分中国学者读了中译本的《原始思维》后又引用该书中的观点去分析《史记》,形成了一种东方主义神话的阐释循环。
《原始思维》把原始人或土著人的思维看成与文明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把原始人的“成年思维”等同于文明人的“儿童思维”。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方式特征是神秘的和前逻辑的,可见,他在“原始思维”和“文明思维”之间划定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对此,人类学家做出了回应,例如,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都可以认识同样的逻辑规则,而且所有的人都将这些规则应用到他们的日常事务中。再如,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Paul Radin)认为原始人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认为,甚至西方人引以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人手,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世界观、生命观等思想对西方哲学范式普适性价值的影响。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观念。拉定以毛利人为例,说明了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E.E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则分析了列维一布留尔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所在:列维-布留尔的错误部分地要归因于在他最初形成他的理论时,所掌握的材料的贫乏,也要归因于他以牺牲世间性和事实为代价而在好奇与感觉之间所做的双重选择。
此外,在对具体事物的分类认知中也存在着“土著人是如何分类”的争论。例如,一些学者在谈到土著民族对动植物的分类命名时认为土著民族“用名字来称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对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大量的事实,尤其是美国学者康克林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土著人对动植物的认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可循的。
由此可见,关于“原始思维”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随着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作为思维方式认知论的“相对论”观点越来越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
(二)认知人类学——研究“土著人是如何思维”的科学方法论
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看成制度,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成符号,而认知人类学则把文化看成知识,即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认知人类学是研究隐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遗物等中的文化知识的学科。认知人类学家所要了解的是: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组织周围世界中的物质现象、事件和经验的,其中包括从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对野生动植物的分类到抽象事件如对正义的理解。
作为一门具有专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_认知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民族科学”。民族科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人类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民族志强调,为了对土著民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仔细的研究,人类学者要坚持实地调查。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学者走进田野后人们却发现,对同一田野点不同的时间进行重复调查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而这又不能用时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变异来加以解释。这些前后相矛盾的民族志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矛盾的冲突源于雷德非尔德(Robert Redfield)与刘易思(Lewis)之间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场争论。雷德非尔德曾经在墨西哥的一个名叫特泊泽兰的村寨中做过田野调查,并于1930年发表了关于当地人的研究报告。后来,刘易思随一个调查队重访该地,并于1951年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雷德非尔德报告中描绘的是浸染了宗教和家族价值的村社图景,协调与和合作是村社的规范。刘易思的图景则相反,该村庄是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四分五裂的村社,自我利益甚至压倒亲属关系的联结。由于前后两次的研究结果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用时间的差异来加以解释。为此,民族志的真实性成了当时文化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
经过争论,人们发现,传统的民族志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忽视了研究者自身文化因素的干扰。因为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文化观来设计调查方案和分析调查资料,这样就难免使所撰写的民族志存在一定的偏见。为了消除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存在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