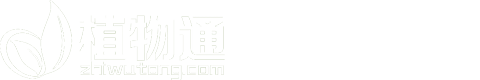植物的智慧
来源:文景 作者:梦亦非 日期:2007-04-01
如果说在《瓦尔登湖》中的梭罗是一个走向内心与自然
质朴生活的诗人,那么到了《种子的信仰》中,则成了一个
怀着诗心的观察者,细致入微地观察了康科德地区许多植物的种子如何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以及哪些动物在传播中起重要作用。

“杨柳轻轻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隋朝无名氏的名诗《送别诗》如此写。可是为何杨柳要“轻轻着地垂”呢?为何杨花要“漫漫搅天飞呢?”“柳条折尽花飞尽”是不是柳树的痛苦呢?诗人可以被这些问题弄得啼笑皆非。但是,从梭罗的《种子的信仰》一书中,我们可以给这些无厘头问题找到正确的科学答案。
“杨柳轻轻着地垂”,原因是柳树在它的传播后代的方式中,这是一个前提。柳树可以通过枝条进行繁衍,如果将随手折下的柳枝播在地上,它往往可以长成为一株美丽婀娜的柳树。为了让枝条繁衍的方式更被世界所接受,柳树必须将它的枝条进化为柔软的绳子状,并且尽可能地下垂。下垂是为了人或动物可以折到,可以被掉到流水中被水带走,柔软是为了可以派上用途。比如人们用柳枝捆绑东西,一旦到了异地解开东西扔掉柳条,那柳条就可以落地生根,从而实现了传播的目的。“红皮柳作为一种外来树种,进入这个地区纯属偶然,前些年人们种树时,有捆树苗是用红皮柳的柳条捆着运来的,其中有个好事的园丁就把这根柳条插到地里,结果现在我们这就有红皮柳,而且还子子孙孙地繁衍不绝。”“柳树与河边其他树种一样,每根枝头的根部都很脆,稍微碰一下就能齐齐整整地折断……就是这种柳条,也能像种子一样散落、漂走,停到哪里就能在哪里落地生根。”这也是柳树在地球各处都出现的主要原因,想想人类的流动,想想中国古代折柳赠别的习俗,再想想柳树总生长在水边,不难明白为何凡有水源处都有柳树的现象了。
“杨花漫漫搅天飞”。这里的杨花不是指白杨树的花,指的还是柳花。柳花之所以要搅天飞,那是因为它要传播它的种子。除了通过枝条传播之外,扩散种子是柳树主要的传播方式。按梭罗的观察,“一条柳絮上能有二十五到一百个微小的籽荚,每个籽荚都呈卵状,带喙,里面是柳绵的紧紧包裹之下,便是无数的种子。”一旦“枝上柳绵吹又少”(苏轼《蝶恋花》),“柳树的种子成了所有树种中浮力最大的,即使在风力极小的时候也能沿着水平方向飞个不停,而下降速度又极为缓慢。”所以“杨花漫漫搅天飞”。梭罗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肯定不曾受中国古代关于柳的诗词的暗示,但他的文字正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折柳、柳絮的原因。

普林尼认为柳树种子在还未成熟之前,就驾驭着蛛丝般的柳絮四处飞散了。荷马的《奥德赛》中写引着奥德修斯进入冥界的喀耳刻这样说:
这里距大洋的尽头已然不远,那里有倾斜的海岸与大陆相连;幽深的杨柳是冥后播下的贫瘠之树,波浪滔天,棵棵都为之失色踯躅。
“贫瘠”一词正好说明了柳树的适应性极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与它的枝条传播、种子传播相吻合。以致于那枝条被行人带到了冥界,那种子被风吹到了阴间。
除了柳树种子的传播,《种子的信仰》介绍了许多植物的种子传播方式,比如桦树种、白蜡树种、铁杉种、樱桃种等等;种种传播的方式:风媒、水媒、动物媒等等;以及各种传播种子的动物:松鼠、松鸦、朱顶雀等等。如果说在《瓦尔登湖》中的梭罗是一个走向内心与自然质朴生活的诗人,那么到了《种子的信仰》中,则成了一个怀着诗心的观察者,细致入微地观察了康科德地区许多植物的种子如何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以及哪些动物在传播中起重要作用。
按照梭罗在行文中透露出的诗性想法,植物为了传播,进化出种种适宜于媒介传播的物种特点,柳枝的易折下垂、松籽上的翅翼、鬼针草籽上的“箭头”……植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意识生命,它们靠着本能产生出有利于后代的传播工具,并且“有意识”地为适应水流、风力、动物而变化,或加强某方面的长处。这种奏效的本能,也就是真正“智慧”。也就是说,植物是有“欲望”的。而植物的“欲望”要等到一百四十多年后,同样身为美国人的作家迈克尔·波伦方发出遥远的应和之声。波伦的重要著作叫《植物的欲望》,他认为,当人类在种植、改造植物的时候,植物也利用了人类的欲望以实现自己强大、扩张的欲望。波伦说:“所有这些植物所关心的也就是每一种生命在最基本的遗传层面上都关心的东西:更多地复制自己。通过种种试验、失误和纠正,这些物种终于发现了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惑动物——无论是蜜蜂还是人类——来传播它们的基因。”动物的欲望,正是被植物传播的欲望所煽动起来的。所以梭罗笔下的植物种子,都是植物的欲望的成果。
波伦在书中提到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章所提论述的“人工选择”,有意思的是,梭罗也受到达尔文的影响。梭罗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反对阿加西斯的“创造论”。阿加西斯是著名的欧洲科学家,哈佛大学与美国一些机构的红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他认为“物种是不可变的”,“但会突然出现或消失,这与祖先无关”。梭罗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通过对故乡康科德地区植物的观察,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创造是不存在的”。按照我的看法,梭罗属于“传播论”者。这种传播不仅是物种的传播,也包括传播“创造”了植物群落的潜在含义。在人类学上,英国有个“传播学派”,该学派认为人类文明与文化样式主要来自于传播,传播影响了各种“文化群落”。梭罗隐在文字背后的看法倒也与人类学这个学派有类似之处。

盖瑞·保罗·纳布罕认为“在研究他家乡附近种子传播的进化适应的特点方面,梭罗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在梭罗之后的几十年,研究种子传播的生物学家还只是简单地收集祖先留下的一些关于种子远距离传播的极端特例。”虽然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和华莱士在热带岛屿上发现的,但梭罗意识到这个理论也适应于温带,所以以他的家乡为观察对象。应该说,梭罗是一个伟大的对故乡做出贡献的人,不仅有《瓦尔登湖》那样的心灵与生活著作,更有研究家乡事物的科学观察手记与结论。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热爱家乡的人不仅仅是让家乡为更多的人所知,更重要的是了解家乡的事物并记录下它们,以让后来者知道故乡的秘密。
梭罗在世时并没有此书,此书是《种子的传播》手稿与《野果》手稿第一部份的集合。提到梭罗,更多人只知道他伟大的《瓦尔登湖》,以及《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缅因森林》、《科德角》,其实梭罗还有一堆庞大的手稿,仅科学研究上,还有六百三十一页的《野果》、七百多页的1850年代康科德自然环境笔记与草图,三千页十二个笔记本中关于早期北美的记录,六千页日记,两本巨型笔记本中那些阅读自然史的评论。
但《种子的信仰》并不是一本成功的译本,它绝大部分是《种子的传播》,译文质量较差,版式花里胡哨如同小学生读物,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段落重复的现象,仅从译者就有三个人这个细节来看,不可以是一个完善的译本。如果梭罗活过来读到此译本,肯定会气得昏死过去。但对于我等,一册在手也聊胜于无罢。